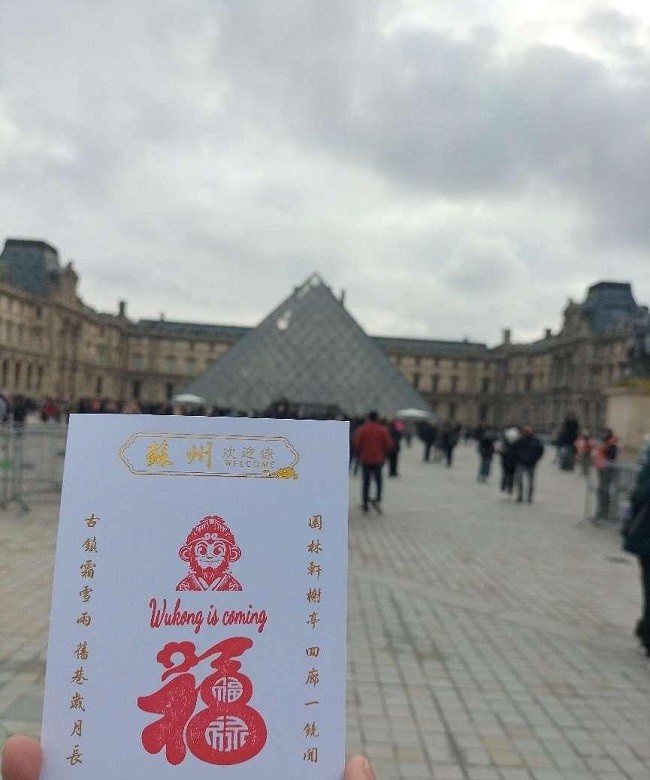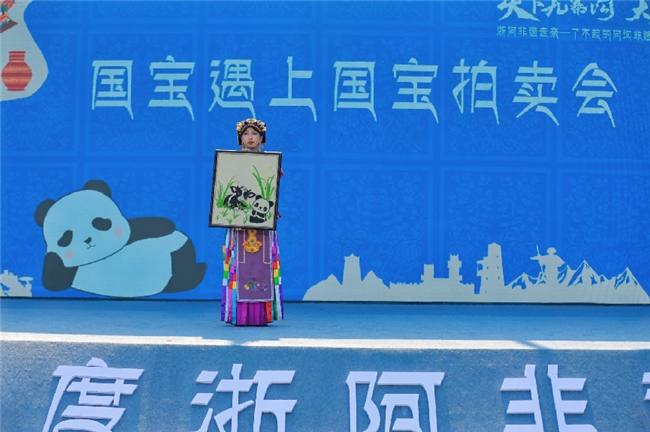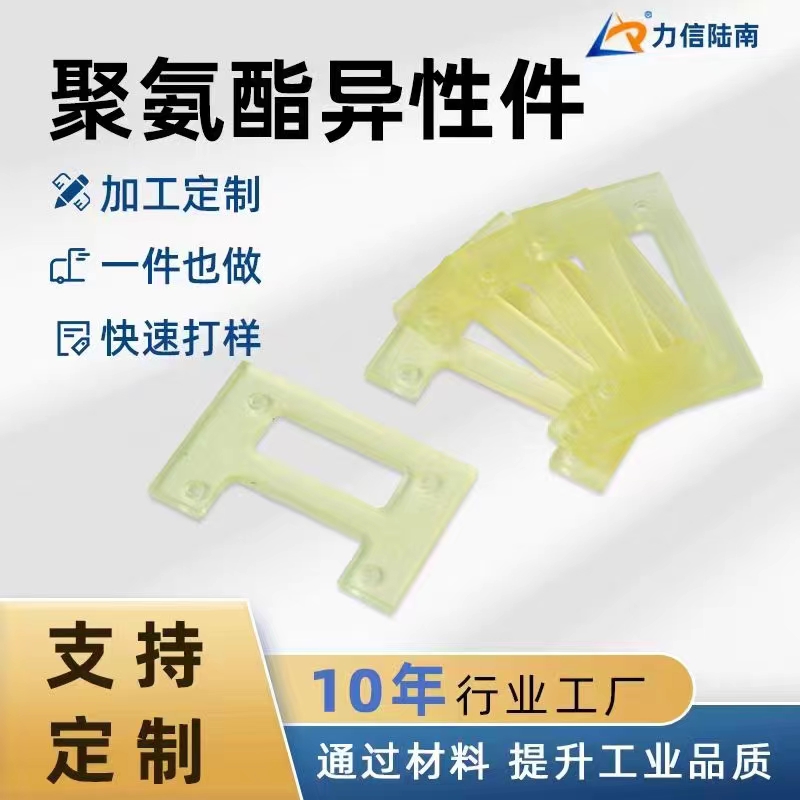多靶点精准狙击:新一代CDK4/6抑制剂有望革新乳腺癌治疗格局
作为临床最常见的乳腺癌分子亚型,激素受体阳性(H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60%~70%,其治疗长期以内分泌治疗为基石,却始终面临耐药、进展等挑战。随着CDK4/6抑制剂等药物的出现,该领域治疗格局不断革新。“肿瘤界”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剑教授,深入探讨HR+/HER2-乳腺癌的治疗现状、对新一代CDK4/6抑制剂的独到见解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问题1:当前,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HR+/HER2-)乳腺癌仍是临床治疗的重点和难点。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该领域最新的治疗格局和重点关注的方向?
张剑教授:HR+/HER2-乳腺癌是最常见的乳腺癌分子亚型,约占60%~70%,内分泌治疗是其长期以来的基石。在早期乳腺癌中,内分泌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强化治疗更能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晚期乳腺癌治疗中,内分泌治疗同样能延缓肿瘤进展、降低肿瘤负荷、改善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存。然而,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均会面临耐药问题——早期耐药多表现为复发,晚期耐药则以疾病进展为特征。
CDK4/6(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抑制剂已成为克服耐药的重要策略之一,获得国内外权威指南如中国抗癌协会(CACA)、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及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指南的推荐。当前乳腺癌已迈入精准治疗时代。越来越多的策略聚焦于CDK4/6抑制剂治疗后或联合靶向治疗,这通常需要依据特定生物标志物,如ESR1突变、PIK3CA变异、PTEN缺失、AKT变异等,以探索逆转或延缓耐药的可能。该领域已涌现诸多临床研究。
同时,我们也需关注新型CDK4/6抑制剂的进展,例如吡洛西利(XZP-3287)。其BRIGHT系列探索包括单药的BRIGHT-1(NCT04539496)研究和联合治疗的BRIGHT-2研究(NCT05077449)。BRIGHT-1研究结果表明,吡洛西利(XZP-3287)单药用于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后线治疗,部分患者可获得良好且持久的疾病控制[1]。目前阿贝西利在国外已获批后线单药适应症,国内我们也高度关注吡洛西利(XZP-3287)在此领域的潜力,因其仍存在临床需求。
问题2:吡洛西利(XZP-3287)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CDK4/6抑制剂,请您谈谈其关键临床研究取得了哪些令人瞩目的核心数据?这些结果如何诠释其在疗效和安全性上的独特临床价值?
张剑教授:BRIGHT-1研究(NCT04539496)是一项由徐兵河院士牵头,在全国29家中心开展的开放标签、单臂、多中心II期研究,旨在探索吡洛西利(XZP-3287)单药治疗在既往接受过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HR+/HER2-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1]。研究数据已于2025年3月发表于Cancer Communications。研究共入组131例晚期复发难治HR+/HER2-乳腺癌患者。针对这一高难治人群(84.7%存在内脏转移,85.5%接受过≥3线治疗),吡洛西利(XZP-3287)单药展现出突破性疗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达11.0个月,显著优于其他CDK4/6抑制剂单药的历史数据(3.8-6.0个月);总生存期(OS)达29.0个月,为后线治疗树立了新标杆。安全性方面,吡洛西利(XZP-3287)最常见的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EAE)为腹泻、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白细胞计数降低、呕吐等,多数TEAE为1-2级,通过支持治疗、暂停给药或剂量调整后可恢复,整体安全性和耐受性在单药治疗中表现优异。
BRIGHT-2研究(NCT05077449)是一项随机、双盲、III期试验,旨在评估吡洛西利(XZP-3287)联合氟维司群治疗内分泌治疗进展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该研究期中分析数据已于2025年4月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2]。最终分析结果于2025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年会公布[3]。研究纳入来自中国64个中心的305例经内分泌治疗进展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其中209例(68.5%)存在内脏转移,78例(25.6%)为原发内分泌耐药,73例(23.9%)在复发转移阶段接受过化疗。中位随访18.99个月,盲态独立评审委员会(BIRC)评估的mPFS为17.51个月(对照组7.29个月;HR=0.462,95%CI:0.333-0.642,P<0.0001)。亚组分析显示一致的PFS获益,单纯骨转移患者HR为0.184(95%CI:0.063-0.541),原发内分泌耐药患者HR为0.337(95%CI:0.191-0.595)。经研究者评估,吡洛西利(XZP-3287)组意向治疗(ITT)人群的客观缓解率(ORR)达45.6%(95%CI:38.62-52.6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4.9%(95%CI:8.56-23.31;P<0.0001)。安全性方面,吡洛西利(XZP-3287)组最常见TEAE为腹泻、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白细胞计数降低和贫血。多数AE为1-2级,可通过对症处理、暂停用药或剂量下调缓解。
总而言之,基于这两项研究,我们认为吡洛西利(XZP-3287)作为中国原研的新型CDK4/6抑制剂,其疗效和安全性数据令人惊艳。同时,我们也期待其在未来新研究设计及真实世界中,进一步展现区别于其他CDK4/6抑制剂的独特价值。
问题3:对于一线治疗进展的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如何制定其后续的用药策略?吡洛西利(XZP-3287)作为CDK4/6抑制剂的重要选择,其“单药适应症”解决了哪些后线治疗中的临床需求?在患者人群选择和安全性管理方面,吡洛西利(XZP-3287)展现了哪些优势?
张剑教授: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无论AI或氟维司群)已成为HR+/HER2-晚期乳腺癌一、二线治疗的重要手段。CDK4/6抑制剂治疗后,后续策略多样。例如,通过精准检测筛选BRCA1/2突变患者给予PARP抑制剂治疗;若存在PI3K/AKT/mTOR(PAM)通路异常,可选择PI3Kα抑制剂、AKT抑制剂或mTOR抑制剂等;或采用内分泌治疗联合其他靶向药物、抗体偶联药物(ADC)等策略。总体原则是尽量减少化疗应用,以控制或减轻其毒副反应。
吡洛西利(XZP-3287)获批的两项适应症分别为:联合氟维司群用于既往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患者;以及单药用于转移性阶段接受过两种及以上内分泌治疗和一种化疗后进展的患者。其在临床研究中展现的整体可控安全性保障了治疗依从性,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作为目前中国唯一获批用于HR+/HER2-晚期乳腺癌单药治疗的CDK4/6抑制剂,吡洛西利(XZP-3287)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当前,在整体CDK4/6抑制剂初治患者中,吡洛西利(XZP-3287)应当可以成为重要的选择之一。在CDK4/6抑制剂经治患者中,未来需要更多数据阐释其跨线治疗潜力,但从前述数据看,应可带来获益。当然,吡洛西利(XZP-3287)单药在真实世界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索。
问题4:CDK4/6抑制剂研究和应用方向将聚焦于哪些关键领域?其在推动精准治疗和改善患者生存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可挖?
张剑教授:目前,以精准医疗联合长程管理的治疗方案正逐步在临床实践中获得更广泛的获益验证。CDK4/6抑制剂在HR+/HER2-乳腺癌治疗中已确立核心地位,其应用场景覆盖内分泌治疗敏感、原发或继发耐药患者,以及一线至后线治疗。尤其在耐药人群中探索CDK4/6抑制剂的跨线应用潜力,但无论采用联合或序贯策略,均需以循证医学证据为支撑,方能实现真正的个体化治疗。若能发掘有效生物标志物筛选优势获益人群,将更有力推动精准个体化治疗。
总体而言,CDK4/6抑制剂未来的应用方向,是在一线、二线及后线治疗基础上进一步夯实辅助治疗数据。目前已有三项辅助治疗研究取得阳性结果,包括NATALEE、MonarchE和DAWNA-A研究。未来关键点在于对这些患者人群进行更精细的亚组筛选。伴随诊断检测也至关重要。未来伴随诊断试剂若能有效上市且商业可及,我们有望在现有CDK4/6抑制剂基础上开展更多探索性联合策略,从而延长患者的无化疗间期。
结语
CDK4/6抑制剂的发展,从早期到晚期、从单药治疗到联合治疗,是一个逐步革新与优化的过程。如今,尽管已有多个CDK4/6抑制剂上市,其应用场景已从最初的“雪中送炭”转变为“锦上添花”,患者也从“有药可用”迈向了“优药可选”的阶段。这一进程促使我们对新一代CDK4/6抑制剂提出了更高要求——它们需要更贴合临床实践,更深入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无论是在临床试验设计还是实际治疗中。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生物标志物能指导患者筛选,使患者获得更持久的生存获益和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